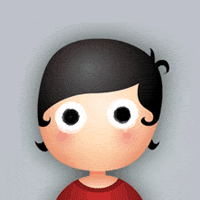《疯人E院》•冯六一•碎镜子
作者简介:冯六一,湖南岳阳人,下过乡、当过兵、做过工,1980年开始发表文字,有作品入选若干选本,诗集《返回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
碎 镜 子
冯六一
这些日子,我经常来到阳台上,默默注视着远处的一片废墟。挖土机已经开始进场了,扬起刚劲的机械手臂,咚咚、咚咚地把东井岭上的泥土掘出了一个大坑。新鲜泥土散发着清爽气息,裸露出来的时候,好像是强健的肌肉被剖析,能看到那些截面细密匀称的肌理。泥土的颜色有些混杂,似黄似红似褐,搅拌成一团厚重的色块。细细地感受,泥土表层的熠熠光泽似乎在往身体里收敛,沉实而又冷峻,凝集了一种内在的力量,仿佛要把我们吸入无边黑暗之中,那里有神秘而迷人的景象。
东井岭上1960年代修建的船工家属平房终于拆掉了,出门随意和左邻右舍打招呼拉扯的日子一去不返。红砖瓦屋里的琐碎生活已经逝去,随之而去的,还有一种几十年聚集起来的混合泥土鲜润气息,参杂身体熟悉味道,可以称之为朴素,也可以称之为俗气的情感。听说这个项目的几个老板有的想做高层,有的想做七层,有的想转包,自己闹翻了,上了法庭,都无暇顾及造房子的事情了。只有守材料老者的影子在工地上时长时短晃荡,偶尔有提袋子收荒货的人停下来,眼睛朝工地上堆积的废旧物品张望。
我家从街河口搬到东井岭的时候,我已经快到上学的年龄了。东井岭的东边是帆船社的家属平房,西面是子弟学校和邮电局的家属房子,酱厂和湘粉厂在岭子的南边,北头是一爿老民居。岭子中间围着的一个院落有些神秘,架设了许多天线,一般人不能进去,是传送广播信号的中波台。东井岭泥土裸露的地方,几乎都被脚步夯实成了泛出亮色的巷子,而被各种植物覆盖的,则潮湿松软,散发着草木和土壤清淡的芳香。东井岭高低不平的地形,使依势错落的民居,在一种无序中显露出层次。那些建筑物舒展的线条,一点也不散乱,像一条条不声不响细小的水流,朝着自己的方向汇集。这些房屋的基脚,深入泥土之中,也像地面的植物一样长出了众多的根须,深深地吮吸地气,涵养着寻常日子的生机。
面对熟悉而即将消失的场景,我心底充满了一种惆怅和茫然,目光在凌乱不堪的废墟上逡巡,试图搜寻到一些值得留驻的东西。一场春雨刚刚过去,嫩黄的阳光散淡,披覆在房屋和巷道杂乱的物体上。东井岭的春天显得稀稀落落,像几只绿色的鸟儿栖息在远处几棵树木上。那些零散点缀的浅浅绿色,由于挤夹在丧失生命律动的水泥楼群中,树木蓬勃的激情被压抑,显得慵懒而有些许凝滞。工地上到处是废弃的门窗、砖块、白灰、电线、水管、塑料,只有一间房屋没有拆除了,孤零零像一蓬乱草丛中的鸟巢。
我游弋的眼睛在一片破败中感到疲乏的时候,忽然被一束散乱的白光刺了一下。在一堆凌乱的砖块边,那白色的光影向着各个方向迸射,毛茸茸的光片,折闪碎碎的星点,时而强烈,时而微弱。这是一面破碎了的镜子,不知是岭子上谁家遗落的。它已经失去了悬挂的高度,失去了方正圆满,以一种破裂的形态接近泥土了。
这样的镜子我见过很多,非常普通,几乎每家都有,或方或圆,悬挂在平行的墙面,摆放在桌子窗台上,抑或藏在女人随身携带的包里。镜子更多属于女人,是她们最钟爱的物件之一,每日里擦拭得明明亮亮,时不时拿出来照一照,好像是惦记镜子,其实是惦记自己,惦记在别人眼睛里的自己。水应该是最初的镜子,也许人从水里窥见了镜子的秘密,后来又发明了铜镜,水银镜。寻常的镜子在生活里,不仅仅使人修饰自己的细微之处,还可以在观照的同时,看见许多无形之物,体悟深藏的内心。人与镜子对视,看见的往往不是镜子,而是人自己。镜子有土地一样的深度,里面藏着一片莫测的海。但每一面真实的镜子,都只能反射局部的影像。大象无形,大镜也无形,无形的大镜无所不在,无所不包,那应该是天地之眼了。
传说两千多年前,罗马舰队进攻意大利雪拉库斯城,已经到达了西西里岛岸边。面对海面上强大的敌人,科学家阿基米德利用镜子聚焦起火的原理,让许多士兵手持磨光的镜子在岸边列成弧形,组成了一面巨大的凹面镜,将太阳光聚焦到一点。当罗马人嘲笑他们怪异的举动时,一道强烈的光焰突然从天而降,罗马人的战船瞬间燃起熊熊大火,士兵被烧死,战船被烧毁。小时候听说这个故事后,我们在东井岭上也做过镜子取火的实验。夏天的中午,几个孩子拿着家里的镜子,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同时聚光,照射一页从作业本撕下的纸。从镜子上反射的光片在纸页上跳跃,但头晒得要冒烟了,纸却始终没有燃烧起来。这样的试验结果使我们对阿基米德故事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。
镜子似乎还有另一种用途,——悬挂在某些人家的门楣,镇宅辟邪。东井岭上敬奉菩萨的尹娭毑,家里摆着一个神龛,常年香火缭绕,墙面被熏得起了一层青色的油垢。。白天,镜子反射出一道清亮的明光,好似一柄锋利的刀刃;即使夜晚,镜子隐约的光亮,也像潜藏的眼睛,盯视着黑暗的深处。简单不过的镜子,在大门口辨识正邪,驱除魑魅,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守护神。尹娭毑经常在纸上蘸水划几道符咒,口里念念有词,把纸焚烧后扬弃在空中。尹娭毑敬奉菩萨,她真有一颗菩萨心肠。七十多岁的老人,把整条巷子打扫得干干净净,花坛侍弄得红红绿绿。有时谁家小孩子不舒服,哭哭闹闹,她过去瞧瞧,说是受了惊吓,晚上独自在屋里,为孩子收吓,弄得有些神神秘秘。
废墟上这面破碎的镜子发出的点点白光,不像泥土的光泽往内收缩,而是极力地往外张扬呈现。在这种暗暗的泥土和明明的镜子之间,通透的光片里,细微尘物轻轻飘舞,姿态万千。空气中几乎没有一丝风儿溜达,几棵孤独的樟树的叶子,屋外晾晒的衣服被单,静止不动,那些沾粘的气味慢慢渗入,平和而安逸。
东井岭原来是荒山野岭,除了几栋青砖黑瓦的老房屋,其余的橘红色砖瓦平房,都是1960年代以后陆陆续续建起来的。帆船社后面一栋家属房做起来的时候,几个民工正在整理地面,一间新房子里的泥土像被什么所吸引,忽然往下陷落了。好多人去看热闹,那些泥土的边缘,像掰开一样,很不规则地下垂,裂开的缝隙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洞穴。那个地下的空间不知隐藏着什么,我看到一片纯黑,像一个不见底的深渊。洞穴越来越大,跌落的白光和泥土里的黑色相撞,然后慢慢地融汇交织,形成一道若明若暗的光柱,像舞台上的追光,在寻找暗处的舞者。泥土里散发着一股木头腐朽的气息,隔绝太久的残败,浸染了土质的鲜润,已经了无生机了。黯淡的青色,由于上下空气的流动,腾起一团光苗忽闪,人们隐约看到了一些白色的骨骸。
原来这是一个荒塚。想想当年,外面一条路径,到这里就断绝了,像是横亘着一道不可触犯的律条。一个半圆的拱顶,是一片虚构的真实天庭,没有日,只有夜,在一种不变的清净里,灵魂的眼睛永远仰望,仰望无尽微妙的天宇。人死后为什么保持着这样一种姿势,是自觉生命的脆弱和卑微,还是渴望着与万事万物交流。生活的谎言都被丢弃在迢迢奔波的路上了,欲火已经熄灭,生命隔绝了和这个世界缠绕的丝丝缕缕,达到一种消亡自己的大化之境。这个上世纪六十年代暴露于东井岭某个房间的洞穴,使我看到了一种纯粹的黑光。我觉得什么光亮都有边界,只有黑色无边。那黑色的光亮,像一面极具穿透力的镜子,洞悉着世间的一切。
水上四处漂泊的船工在陆地上有一个安身之处不容易,但谁也不愿意分到的新房子里面有一座野坟。大家只能抓阄。管后勤的晏爹把写好房间的纸捏成坨,放在竹篮子里,盖上一块蓝布,笑眯眯地说,摸吧,冇得办法,认命。一只只手探进竹篮子,又慢慢把拿到的纸团扯开。摸到这间房子的人满脸懊丧,爆了一句粗口:嬲他娘,倒血霉!不要!他放弃了这次分房的机会,宁愿继续排队等待。尔后,一个栖身船上的年轻水手急着结婚,找个对象不容易,管它呢,住进去再说。窗玻璃贴上了红彤彤的“鱼嗦莲”和“喜鹊踏枝”,大门贴上了红彤彤的双“囍”字,满屋挂上了五颜六色的彩带,一帮船上的伙伴们喝酒打牌,哦呵喧天闹腾了几天。他后来还真是兴旺起来了,靠着跑水上运输,采河砂办砂场,成了古城有些名声的富家。
东井岭上除了颜色混杂的泥土,我还看见过生长的石头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“深挖洞,广积粮,不称霸”,神奇的国土上不知道挖掘了多少洞穴。东井岭也不例外,男女老少都加入了这场挖掘地道的行动。在芦席厂的南面,有一片裸露的岩石,顺着岭势往上倾斜,裂开的缝隙,流泻粗壮的线条,像一丛锐利的刀锋,也像一林茂密的竹笋。这是一片正在演化的岩体,比泥土坚硬,比石头脆弱,处于一个生长的过程,应该还是岩石的婴幼期。剥落的岩体,细伢子们常常拿来当粉笔在地上乱涂乱画。
我们避开这片生长的石头,在一片杂乱的树木遮掩的地方,找到一处松软的泥土,开始挖掘地道。每家都分派了任务,轮换着来挖。泥土与铁器接触的表面,一条条痕迹光滑锃亮。鲜润的泥土,被锄头一块块切削,好像还存着体温,农人在土地上收割作物,我们土地里收割着泥土。干干净净的泥土用竹编的箢箕拖出洞外,运往一处空旷的洼地。由于开掘的空间低矮窄小,只得把锄头的长柄踞掉一节,有时还要屈膝在温润而生硬的碎泥上,一下一下慢慢来刨。岭子上的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像一只只坚硬的穿山甲,不断地重复这样的动作,历经数月,两条在地下蜿蜒的地道形成了。一条是从芦席厂后面的岭坡通往华华家的后门和小林家的后门,有两个出口;一条是从岭子西边京广铁路的墈边,在泥土之下穿过斜坡的一片菜地,通往子弟学校一间房屋里面。
地道修好后,这里成了岭子上的孩子们探险和比试胆量的地方。一个人带着一盒火柴,不许结伴,只能独自穿越黑咕隆咚的地道。好像整个东井岭地下的湿气,从泥土那些细密的缝隙找到了聚集的地方,地道里阴冷森森。洞顶时不时有水珠滴落,叮咚叮咚,隐隐约约,像有人在幽暗的深处喃喃自语。偶尔还有老鼠从身边蹿过,弄出一串仓促的声响,惊得人一身寒颤后,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水滴在洼地积聚成了水潭,像一面面黯淡的镜子,照出模糊的身影。点燃一根火柴,可以行进数米。那小小的光焰,被地道里的黑暗裹住了,又把黑色掘开了一个洞穴。这重叠的洞穴,像俄罗斯套娃,一个比一个细小,直到微弱的火灼痛手指后慢慢熄灭,世界又又陷入惊恐的黑暗之中。赶紧掏出一根火柴棍,慌乱地在火柴盒边子上一划,吱的又燃起了一团光焰。在不断消耗火柴的过程中,心理渐渐适应了黑暗,即使没有火光和黑色浑然一体,也不像刚进入地道时感到恐惧,碰触虚无的黑暗,倒萌生了些许奇幻,那里面不知道隐藏了多少秘密。离出来的洞口越来越近,光线越来越强烈的时候,感觉好像是从母体的子宫里探出,看到了一个新奇的天地。当黑暗完全从身体上褪去,孩子们不知不觉发生了一种蜕变。人就是这样一次次历练,激发了生命潜藏的能量,一点点去破译世界的隐秘。
燠热夏天,地道是岭子上人们歇凉的好去处。一股股沁凉的冷气在洞口弥漫。一天中午,太阳晒得树叶低垂,知鸟都停止了聒噪,我和一个小伙伴钻进了地道。一个僻静的拐角,竹铺上躺着一对男女,两件白白的背心挨得紧紧的,那种棉布的白色在不甚明亮的地方,像在水上漂浮,时隐时现。许多心性都要隐忍的年代,这样的情形显得大胆而新异,像密室里一幅对情爱献祭的图景。从地下穿越的洞穴,暗暗的,正好提供了人们需要的这种隐蔽性。我和小伙伴相互一望,伸伸舌头,做个怪相,扑哧一笑,转身跑出了地道。
从京广铁路边上进入的地道,我发现过一个秘密。洞门的锁锈坏了,我一个人钻了进去。划着火柴走了近百米,有一节水泥台阶,我轻轻顶开掩盖地道口的木板,爬上来一看,原来学校的传达室改成了临时放图书的地方。看着满屋的书籍,我当时的惊喜不可言说,悄悄地在里面翻看了一两个小时后,走时拿走了一本薄薄的《陈玉成》。上个世纪7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版本。红色封面,缠着头巾的陈玉成,身姿前倾,飞舞着一把大砍刀,粗厚的线条,有木刻意味。选择这本书,不是多么喜爱这位年轻英俊的太平天国的将领,是因为在书中翻看到了一段文字,陈玉成在洞庭湖汇入长江的城陵矶,与曾国藩的湘军展开过一场血肉迸溅的厮杀。城陵矶历来是兵家重地,我坐父亲单位的客班船到过那里。荆江、扬子江、湘江交汇的三江口有一条时刻变化的水线,清浊分明。蜿蜒的长堤边柳树依依,对岸是绵延不尽的芦苇荡。看到熟悉的地方出现在一本书中,很惊喜,猛然觉得历史就在眼前一样。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如今,隐秘的地道早就废弃了,好像那些年代的那些激情那些物事,已经隐入了时间深处。东井岭废墟上残存的那间房屋,是唐莲子家。她来自长江北岸的洪湖,嫁给驾船的周师傅后,在南区的“三八连”拖板车。矮小的身子,每天拉着货物满城跑。现在也已经80多岁了吧。,现在政府每月给一点补贴。大女儿和二女儿已经做奶奶了,但是她的小儿小女,四十多岁了,成天不出家门,成了名副其实的宅男宅女,全靠着她的一点补贴和低保金过日子。前些年唐莲子每天提着个蛇皮袋,到处去捡拾废品,补贴家用。岭子上的人说她开出的搬迁条件是要两套房屋,除此之外,一切免谈。谁要是断水断电,她就拿着菜刀去追,颇有幼时遗风。
过去的生活无法还原,已经断裂成了星星点点的碎片。但那面遗落尘土上的碎镜子,像过去的日和月,像过去的眼睛,在行将被黑暗淹没之前,仿佛还在窥视着什么,而诱惑我们叙说的语言,同样面临着破碎的危险。